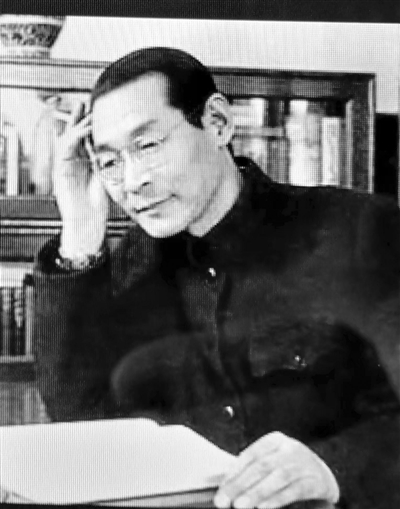

①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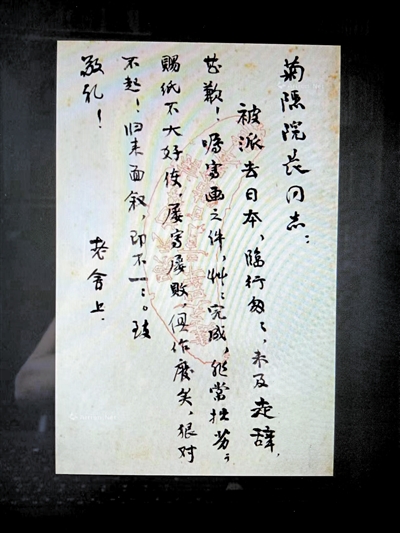
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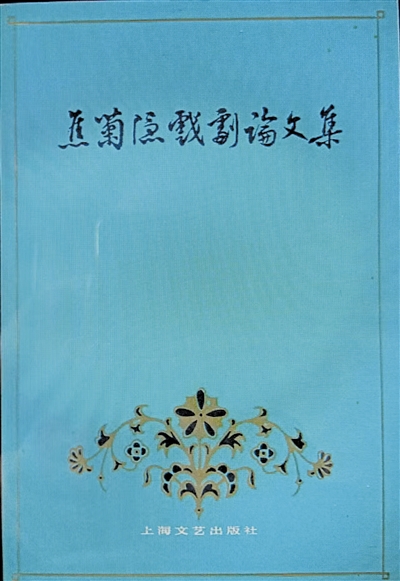
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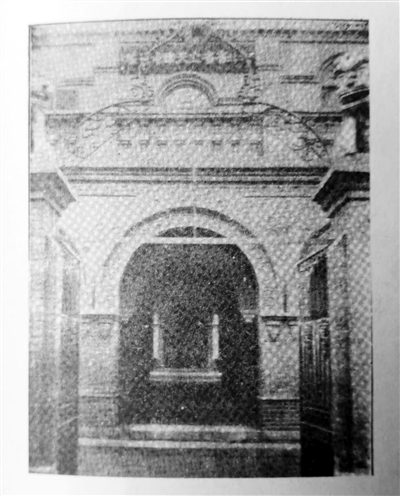
⑥

⑦
焦菊隐(1905—1975),原名承志,曾用名菊影,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官宦之家。焦菊隐对中国古典戏曲和西方戏剧都有精深的研究,是著名戏剧理论家、导演艺术家、教育家、翻译家,是北京菊影戏剧研究中心发起人,还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和艺术上的奠基人之一。在话剧舞台艺术实践中,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他的导演创作方式对形成剧院的艺术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善于吸收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手法,融会贯通地运用于话剧艺术,在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焦菊隐是喝海河水长大的。他的成就与他在故乡天津的成长以及青少年时代在天津接受的教育、良好的戏剧氛围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艺术生涯发轫于天津。
一、家世由望族到社会底层
焦氏家族世代居住在金钟河锦衣卫桥的火神庙附近(今属河北区),是天津的老户人家。早年的焦家大院占地百亩,门楼临街,墀头砖雕极为考究。其门后为砖砌影壁,后为穿堂式门厅。其后为箭道,沟通东西两座大院。东院由六套四合院组成。两院建有佛堂,另设跨院,为佣人和杂役住室。庭院后面构筑园林。
焦菊隐的高祖焦景新(1763—1831),字景川,号午桥。清嘉庆六年(1801)进士,授吏部主事,升郎中,改监察御史。曾出任江西饶州知府。《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三十四《贤能传》中有焦景新传,其中提到:“武清煤厂镇有牙侩为市场害,奏请查办,民至今便之,勒碑纪其事。”记述了200年前津北梅厂镇设立集场的一桩往事。
今武清区梅厂旧时叫煤厂,清代属顺天府武清县管辖。嘉庆十九年(1814),有李姓乡民提出,附近村庄离各集镇太远,又因河堤被冲决,肩挑背负者往来甚艰,于这年春呈明该县知县,在煤厂一地设立集场,经知县批准,实行数月,乡民感到十分便利。正在这时,杨村集镇某牙侩认为,在这儿设集场势必分己之利,遂从中阻挠,寻衅闹事。该县知县受其要挟,心生畏惧,又将集场撤掉,百姓怨声载道。
当时焦景新正担任监察御史,得知这一情况后,做了进一步调查,他认为:“设立集镇,原取适中处所,为农工商贾萃聚之区,并非为牙行经纪牟利之薮。”于是他上奏朝廷“相应请旨,饬顺天府府尹派委妥员,详悉确查武清县煤厂地方,添设集场果否便民”“据实详报府尹,以凭核办”。后经顺天府查办,煤厂镇的集市最终得以恢复。
《天津县新志》记载:焦景新在饶州知府任上,“时有民妇子溺水死,诬人谋杀,久不成巘,景新一鞫而服;余干石虹山产煤,居民争利,纠众械斗,大府檄偕参率兵一二百往捕之,参将欲围剿市功,景新亟止之曰:‘此百姓私斗,非敢反也。’晓以利害,逮为首数人,余悉遣去。”又云“禁革官价,却馈金,在任五年以‘廉谨’著称”。道光八年(1828)“引疾归,十一年卒于家,年六十有九。著有《同文拾沈》《叶韵窥斑》《杂字姓函》《多识杂钞》”。
焦景新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焦佑沄,“举人,官训导”。一个叫焦佑瀛,“举人,官太仆寺卿”。这位焦佑瀛便是焦菊隐的曾祖父。
焦佑瀛系中国近代史上祺祥政变中被罢官的赞襄八大臣之一,当年八大臣反对两宫垂帘听政的皇帝谕旨,便是由他执笔代拟的。焦佑瀛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因其才干超群,于咸丰十年(1860)由静海被召至热河,成为咸丰皇帝身边的要人。咸丰死后,八大臣以清廷祖制和清帝遗命为依据,驳斥所谓皇太后垂帘听政的主张。据称,焦佑瀛被革职后曾隐居焦家大院后面的“逋园”。随着时光的流逝,焦家大院渐被切割成大大小小的民居,现也已不存。
焦菊隐的祖父焦骏声是焦佑瀛的长子,清咸丰八年(1858)中举,官同知。到了焦菊隐的父亲这一代,焦家败落了。他的父亲焦曾宪是个秀才,既没有门路去谋官,又没有本钱和本事经商。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天津,焦家大院大部被烧,焦家全家避难借住在天津北门乡井儿王宅。1905年,焦菊隐就出生在这个大杂院里。这时的焦家已经沦落到社会底层,焦菊隐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
二、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
焦家毕竟曾是天津的名门望族,当年他们家与鼓楼东姚家、李家等大家族是世交,且多有亲戚关系。焦菊隐的叔祖焦骏枫与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李筱楼)同为同治四年(1865)进士,属于“同年”。又由于存在各种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焦家在困难之际受到姚家、李家的援助。后来焦菊隐又是在李鸿藻的三子李石曾的帮助下,创办戏剧学校,进而在戏剧艺术上得以发展。
当年焦菊隐的父亲焦曾宪在亲戚盐商姚家帮账。尽管有一些收入,经济上依然十分困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焦曾宪便把年幼的焦菊隐送到王家家馆寄读。因家穷,焦菊隐受到老师的歧视和富家子弟的欺负。焦菊隐回忆说:“那是一个新派的冬烘,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也很高兴,只是我对老师极不满的一点是他瞧不起我,因为我家穷。他对于王家和其他阔人家的子弟却一再从宽、放纵;有钱的富家子弟欺辱我,他反而狠狠地责骂我。因此,我回家以后,哭着、喊着说再也不上王家家馆了。我父亲没办法,只好叫我停学,并托人送我进一家小学读书。这就是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
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创办于1905年,是天津最早的官办小学之一。据掌故老人回忆,当年这所学校有三四进的大院子,每个院子都是长方形的,中间是土地,四周靠教室有高出地面约二尺的走廊;校舍里教室很多,也很大,敞亮、干净,还有挂图室、音乐教室、宽大的操场。这里先后培养出天津近代十二大名医中的朱宪彝、朱宗尧,著名书法家龚望,著名画家刘子久,经济学家梁思达等大批国家栋梁之材。时任校长刘宝慈(竺笙)不求名利,爱生如子,以校为家,终日操劳,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焦菊隐在这所小学受到了极好的教育。
刘校长不仅关怀学生的成长,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还关心学生家中的经济状况。他认为,没有钱的家庭是很难送子弟入学的,但必须让孩子尽量得到学校教育。当时,官立学校也收学费,常常因为官方的教育经费不足,学校的一切开支都要出在学费上。学费方面,有的学校一个学期要一两块大洋(当时一块大洋能换一百枚左右铜元)。刘校长任职的这所学校虽然有很多学生,每人每学期却只收二十六枚铜元,这当然是不能维持的。但刘宝慈坚持这样做,以照顾穷苦的学生。他一方面尽力节约,另一方面向省教育当局要钱。为此省教育当局常和他吵架,下令叫他增收学费,他都顶了回去。由于学费低,学生家庭负担大大减轻了,焦菊隐也得以在这所小学安心读书,并获得优异成绩,成为“最好的学生”。
在第一模范小学上学期间,刘校长为学生赠“号”的事让焦菊隐永生不忘。焦菊隐回忆道:“每到毕业班大考以后,校长总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赠送每个学生一个号。当时,每人除名字外,还要有一个号,社会上彼此尊称号而不直呼人名。校长从不作训话讲演诸如此类的事。但到毕业班学生要离校的时候,他就以赠送‘号’作赠言。我的学名叫焦承志,他送了我一个号叫‘亮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名叫承志,可是承什么志呢?你不应当承做官发财的志,或者争光耀祖的志,你应当以救国为己任,承强国强种之志,但不能同流合污。你应当学习诸葛孔明。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请他去做官,他不要做官。等到他确实知道刘备的确是想救民于水火,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送你‘亮俦’这个别号,不是叫你学诸葛亮那样去做大官,而是要你能和他一样安心务农。”
焦菊隐曾在《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这篇文章中,怀着满腔热情,以很长的篇幅,颂扬刘宝慈校长,感念这所小学对他少年时代的启迪和教育。他说:“我的小学校长给我思想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首先灌输给我极深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刘校长认真、严肃、刻苦、勤劳、朴实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给我强烈的身教,使我逐步树立起我的个人奋斗目标。”
三、文化艺术生涯的源头
1919年,焦菊隐考进了天津的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受到五四新文化的激励,读了很多介绍“新思潮”的书刊和文章,并参与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组织游行,办学生刊物,组织读书会,安排演戏、辩论、演讲等。在天津,焦菊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底子,天津也是他文化艺术生涯的源头。他在省立第一中学、汇文中学读书期间,考试屡列前茅,早已在朋侪中赢得“才子”之名。读高中时,他呼应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与赵景深、于赓虞等青年人组织了新诗团体——绿波社,编辑《绿波》周刊,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诗,在报刊上发表,并出版了《夜哭》《他乡》的诗集,当时即有“天津诗人”之称。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有记载。
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夜哭》共收入焦菊隐的散文诗《夜哭》及杂诗33首,是中国新诗初创时期的一本重要的诗集。其中《夜哭》一诗写于海河岸边的家中,时为1924年3月12日夜。是“夜正凄凉”,微风“正吹着妇人哭子的哀调,送过河来,又带过河去”。作者被“黑,寒,与哀怨包围”着,“踱过了震动欲折的板桥”,“夜里的哭声颤动了流水,潺潺地在低语,又好似在痛泣”。全诗借黑夜“妇人哭子”的悲惨情景发泄对时代的哀怨和悲愤。哭泣的时代铸就了悲哀的诗魂,凄凉的诗行诉说着人间生命的荒漠。焦菊隐说过:“一方面,我在小学受着这种教育——培养成为一个文明人,将来好富民强种;另一方面,我的实际家庭生活和接触的实际社会人物又是很悲惨的。学校教育是一种空想,现实生活是一种实际。这二者,在我的思想意识上是矛盾着,摆动着,同时在相互争取着我。我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成长着。”
焦菊隐于上世纪20年代的文学创作早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厚重的一页。他的作品不仅天津的报刊时有发表,也在北京的《晨报》等报刊上发表,因此结识了孙伏园、邵飘萍、石评梅等进步青年。
天津是戏剧之乡,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李叔同在青少年时代就喜爱看戏、演戏。张彭春则是中国北方话剧奠基人之一。出生在天津的曹禺,其经典之作话剧《雷雨》《日出》也都是在天津创作、演出和酝酿的。梅阡、梅熹、谢添及于是之、牛星丽等戏剧大师和著名导演、演员也都是生长在天津。在这种戏剧氛围中,特别是受到前辈戏剧艺术大师的影响,焦菊隐自幼就对戏剧有着极大的兴趣,演戏是他最喜欢的。读小学时,他就加入了学校的新剧社演文明戏。他曾与同学组织了一个剧社,自己编剧,在同学家里演出。他第一次演出的戏是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张诚》,他在剧中饰演主角,博得了观众的好评,这是焦菊隐从事戏剧活动的开始。他回忆说:“首先是南开新剧社在1915年、1916年左右开展的反封建、反阶级压迫的新剧运动,它的力量也冲击到小学里来。当时,我们也组织了一个新剧社,轮流到各家中去演出……剧本都是自编的,内容以反封建、反压迫为主。”又说:“我被派名叫‘菊影’,后来因为这太像演文明戏的名字,又改为‘菊隐’,这个名字一直被称呼到今天,想改也无法改了。”(《菊隐艺谭》)从那时起,戏剧便成了焦菊隐一生奋力追求的事业。
四、戏剧艺术成为终生追求
1930年,焦菊隐在燕京大学毕业后不久,得焦家世亲长辈李石曾之助,在北平创办中华戏剧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一改过去旧科班制和旧梨园界的诸多戒律,以崭新的教育方式培养有文化、有教养的戏曲演员,并实行男女合校,对中国戏剧教育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创新。在他当校长期间,先后收了“德”“和”“金”“玉”四个班,当代著名京剧演员傅德威、李和曾、王金璐、李玉茹、白玉薇、高玉倩等,都是当时的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焦菊隐在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后回国,在广西、四川等地从事戏剧教育和抗战宣传,先后任广西大学、广西教育研究所、四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重庆社会教育学院、西北师范学院教授,直到抗战胜利重返故都,在北平师范大学执教,任法语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参加导演了《夜店》《上海屋檐下》等话剧,轰动一时。他精通英、法、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在执教的同时,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他在深入研究中国表演理论和表演体系的同时,刻苦钻研外国表演体系和戏剧理论。1947年,他创办了北平艺术馆。1948年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焦菊隐一度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出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从事他最喜爱的戏剧事业。他善于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和新兴的话剧艺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的戏剧艺术体系。他要求演员在舞台演出中,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他在导演艺术上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风格,创立了具有民族气质的导演学派。他先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过蜚声艺坛的老舍剧作《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以及《关汉卿》《虎符》《蔡文姬》等剧目。
1975年,这位对祖国文化艺术事业无限热爱的艺术大师悄然离开了人世。焦菊隐在世时,总爱说:“我喝遍天下的豆浆,哪也不如天津的豆浆好喝。”那是他思恋故乡的代名词。如今天津的豆浆还是那么浓郁、芳馨,而被天津豆浆哺育大的一代艺术大师焦菊隐,让家乡人骄傲的则是他对话剧艺术发展的不懈追求和长久贡献。
图①青年时代的焦菊隐
图②菊隐剧场揭幕
图③焦菊隐少年时就读的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
图④老舍致焦菊隐的信札
图⑤《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图⑥焦菊隐就读的天津省立第一中学
图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