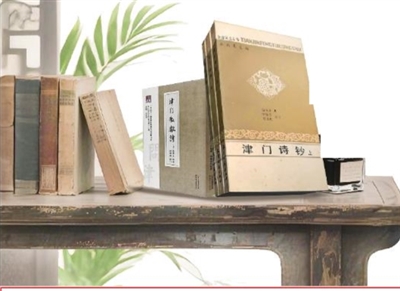
津派文学的再提出
2024年10月,天津市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会议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召开,第一次从政府层面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津派文化,要求彰显河海文化特色、擦亮红色文化底色、传承建筑文化风格、赓续工商文化基因、创新民俗文化形式、活跃演艺文化氛围、释放文博文化活力、深耕休闲文化土壤,努力打造特色鲜明、内涵深刻的津派文化品牌。这也为我们立足新时代,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重新回顾和审视津派文艺和津派文学,推动其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视野和明确指引。
天津,居内河外海之要冲,聚五方杂处之繁庶,历史肇造久远,风雅流传不绝,故文运盛、文脉广、文缘深、文蕴厚、文气足。由之孕育的津派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一般而言,津派文化狭义指文学、绘画、戏曲、影视等具体艺术门类的天津流派,起源于古代,发展于近代,繁盛于当代。后来内涵拓展、边界延伸,成为广义的津派文化,包括风土人情、衣食住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非遗”乃至审美情趣等在内,涉及长期以来在津沽大地上积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两种文明。纵览华夏文化版图,天津作为京剧的大码头、评剧发祥地、北方曲艺之乡、中国话剧摇篮、歌唱家摇篮等,名家辈出,精品荟萃,不仅在近代文化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也形成了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津派文化。可以说,津派文艺是津派文化的核心部分和生动体现。
其中,津派文学又称津味文学,或特指津味小说,是津派文艺、津派文化中最为广泛认可的区域流派。历史上,硕彦名儒、诗人骚客往往以壮燕游望东海、乘天风泊天津为人生极大快意之事。明代以前,史书遗阙,文献少存,天津文学多为咏物吟景、纪游酬答的散章短篇。明永乐初年,天津先后设卫筑城,开始出现正式的天津文学。这一时期的天津作家,在嘉靖之前以流寓文人为主,自嘉靖之后本土文人才开始增多。晚近以降,天津崛起为大都市,文学著作便如恒河沙数。近百年来,天津作为中国文学重镇,更是名家辈出,佳构频现,涌出一批批反映时代发展、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名家名作。若重新从文化与地域的视角溯端竟委,可以见出自清以来,津派文学历经孕育、发展、新变、繁盛和深化等阶段,进而形成了津味十足、文脉悠长的传承谱系。
津派文学的远源
清代是津派文学的孕育期。自明入清,天津文学呈现出繁荣态势:众多文学家族涌现,地域性文学总集增多,古典文学诸体兼备,新兴文体开始出现,戏曲文学逐渐成熟。天津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最为显著者,是天津本土意识觉醒、地域作家群体出现。其中,如《津门诗钞》《津门文钞》《津门古文所见录》《津门竹枝词》《津门徵献诗》等标榜“津门”的地域类文学总集大量涌现。清人梅成栋《津门诗钞弁词》曾论:“津门汇九河之秀,萦纡注海,气之所蓄,必有所钟。明代甲科辈出。本朝二百余年,斯文益盛。”在此期间,天津出现了张氏遂闲堂、查氏水西庄等文学家族和作家群体。尤其是查为仁等水西庄几代主人,广揽天下文人墨客,宴游觞咏,诗文赠答,形成了庞大的水西庄作家群体。他们以卓越的创作实绩、强大的创作队伍,使天津本土文学真正跻身并融入全国文学主脉,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天津文学独立发展和兴盛的重要标志。
近现代是津派文学的发展期。天津开埠之后,城市地位日渐提高,其反映在文学领域尤为突出者,一是天津本土作家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越来越高,二是大量的文学之士奔赴天津寻求变革和开拓。严复、梁启超、李叔同、严修、曹禺,以及宫白羽、刘云若等,立足津沽、放眼全球,大力推动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型。严复曾在天津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并以信达雅之笔,最早翻译发表了《天演论》的部分章节,影响深远。当时经济的繁盛和报业的发达,还促生了影响全国的北派通俗小说。其中,宫白羽被誉为“一代武侠小说的宗师”,他的《十二金钱镖》《偷拳》等小说演绎侠义精神、叙写世态人情,俞剑平、杨露禅等侠客义士形象深入人心。刘云若则用一个“情”字贯通《春风回梦记》等数十部言情小说,因其小说数量多、流传广、影响大,刘云若与张恨水齐名,被称为“南张北刘”。他的《小扬州志》等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天津市井特色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天津独特的地方风俗民情,“津味”十足,在整体上提高了津派小说的文学品位。戴愚庵的《沽上英雄谱》《沽上游侠传》等小说则专写天津“混混”。对此,范伯群先生曾评论道:“刘云若的《小扬州志》等作品和戴愚庵的《沽上英雄谱》《沽上游侠传》等‘混混小说’就是天津的都市乡土文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津派文学构成了后来津味小说的远源。
津派文学的近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津派文学进入新变期。天津解放后,孙犁、梁斌、方纪、王林、鲁藜、杨润身等大批来自延安和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天津。时任晋察冀群众剧社骨干的张学新,在他的《进军天津日记》中曾兴奋写道:“天津解放了,人民翻身了!我们要同人民一起,同心协力,恢复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新天津,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些文艺工作者往往既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新中国文艺的创作者,进城之后在天津传承发展延安文脉,在文坛上也“建设起一个新天津”,为天津当代文坛带来了全新格局——形成了新的文艺创作主体,创办了新的文艺传播载体,构建了新的文艺管理体制,创作了大量新作品、塑造了系列新形象,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新导向。
这一时期,天津工人文学迅速发展,无论是文学创作成就,还是工人作家队伍,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新文艺来说,工业题材文学尚属于新兴的文学创作领域。但是,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培养工人作者、发展和繁荣工业题材文学方面,却较早地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天津当代文学的新传统。如孙犁曾创作了关于天津城市和工业建设的系列散文速写,后收入《津门小集》。天津文联主席阿英主编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先后出版25种,收录了王昌定、鲍昌、阿凤等人的作品,也集中显示了这一时期天津工人文艺创作的成绩。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则是当时国内首创的由普通工人组成的业余文学创作团队,曾得到茅盾、周扬、丁玲等人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植,发掘培养了万国儒、董乃相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工人作家。周骥良的《我和工人文学社》曾回忆:“工人文学社的几篇作品打响,誉满京城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评论家邵荃麟特地听了一次有关工人文学社的汇报,他很振奋也很感慨,说30年代左联在上海成立,想找一两个能写工厂生活的工人业余作者,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想组织一个工人文学社团,更是近似梦想的空谈,万没想到二十年之后竟然在天津实现了。”后来的蒋子龙与肖克凡等人,则将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无论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是新培养的青年工人作家,都非常熟悉并有意使用带有津味气息的方言词语,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津味文化的独特性,对改革开放以来津味文学的形成发挥了奠基作用。其中,话剧《六号门》(原名《搬运工人翻身记》)以反映旧社会搬运工人的生活为主,素材来自工人、演员来自工人,甚至直接用工人的原话作为台词,公演后,广受欢迎,先后演出近百场,又改编成京剧和地方戏,并被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一时间风靡全国。可以说,当时以《六号门》等为代表的津派文学,注重书写地域风俗和风情,善于使用地道的津腔津味,对后来的工业小说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也是中国文坛上津味文学的近因。
津派文学的繁盛
改革开放以后,津派文学进入繁盛期。从冯骥才、蒋子龙、刘航鹰、林希,到赵玫、肖克凡、王松、尹学芸、武歆等,“文学津军”全面崛起,创作势头强劲,蜚声中外。津味文学自此确立,津味小说更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范式。“津味”几乎成为天津文学最重要的标识。
其中,冯骥才从办刊、评论和创作等方面推动和发扬津味文学,短短十几年间,撰写了数百万字的小说、散文、戏剧和理论著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反响。他的小说《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以及散文《珍珠鸟》等作品,不仅荣获各类全国奖项,还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或被改编成影视等,传播到海外。蒋子龙则力举当代文坛改革文学的大纛,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大潮,“乔厂长”更是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农民帝国》等,更是以真实之笔尽情描绘时代的变革与更新、生活的广博与深刻,不断将津派文学推向新的高度。
此外,刘航鹰先写话剧,继而创作小说,后又投入影视编导。她的《明姑娘》《金鹿儿》《倾斜的阁楼》《乔迁》等,勾勒世相,描摹人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并充盈着浓郁的天津特色,给人以美的享受、爱的深思。林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攻津味小说。他曾说:“我认准了一句话,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艺术空间。写改革,我比不了蒋子龙;写当代生活,我比不了小青年。但我是老天津卫了,祖辈几代生活在天津,对旧天津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天津的旧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觉得一心一意去写天津味比较适合我。”林希先后创作了《北洋遗怨》《相士无非子》《高买》等,注重揭示天津人深层次的心态和天津文化深层次的内涵,刻画豪爽、侠义、热情、朴实、幽默、聪明的天津人形象,为世人展示了天津卫百余年的民俗画卷。
自孙犁、梁斌、方纪等,发展到冯骥才、蒋子龙、刘航鹰等,以津味小说为中心的津派文学,有着代表性作家、经典性作品,大致形成了运用天津地方语汇、刻塑沽上特色人物、展示天津市井风情的整体性风格,并对年轻一辈作家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无论是冯骥才写奇人俗事、林希写能人世事,还是冯育楠写真人轶事、肖克凡写凡人琐事,他们因为精熟于生活、挚爱于本土,所以都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神有态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状态。尤其是,他们深入生活、紧贴时代的人文精神,写作勤奋、态度严谨的专业精神,以及真诚为本、自成风格的独创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也引发了对新津味文学和新津派文学的深入探索。
津派文学的新境界
进入新时代,津派文学转向深化期。天津作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出精品、出人才”,不断开拓津派文学的新境界。
一是作品数量和质量实现“双提升”。据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后,仅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合同制作家就在全国报纸、期刊发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400余部(篇),报告文学100多部(篇),散文、诗歌、随笔3000余篇,评论、论文近400部(篇),话剧、影视剧本300多部(集)。仅2021年,就有13人次荣获全国各类文学奖项。其中,冯骥才《多瑙河峡谷》获《当代》杂志“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尹学芸《鬼指根》入选《收获》中篇小说榜;张楚《过香河》获第十九届全国中篇小说百花奖;王松《暖夏》入选“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此外,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和尹学芸的《李海叔叔》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和中篇小说奖,王松的《红骆驼》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天津作家的不少作品还被翻译介绍到海外,扩大了天津文学的国际影响。
二是“文学津军”队伍更加壮大。截至目前,天津市作协会员数量超过1700名,其中中国作协会员200余名。近年来,为打造建设一流队伍阵地,天津坚持“广泛吸收、挖掘潜力、把握质量、注重培养”的原则,先后实施了培根铸魂、改革强文、高原高峰、文学惠民、人才兴文、融合发展等重大工程,成效明显。如蒋子龙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王松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之“优秀作家贡献奖”,冯骥才、张楚、朵渔获“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奖,充分展示了“文学津军”的雄厚实力。
明代易学名家乔中和解“剥卦”时尝言“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这也道出了津派文学谱系传承不绝的根由。赵玫曾说:“任何的创造性都来自于对自身传统的扬弃,并由此发现并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尹学芸则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有力证明:“生活中处处都是文学素材。”新时代新征程,天津作家将更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挖津派文化资源,不断推出时代特色鲜明、文化风格独特、地域特色浓郁的精品力作,继续以如椽巨笔书写津派文学的壮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