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泥人张”传人张乃英先生的4篇手稿。(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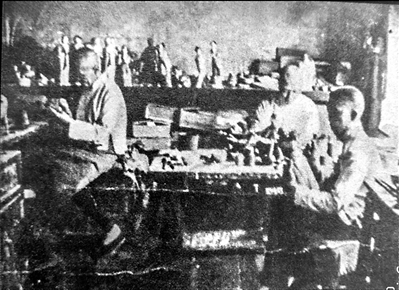
“泥人张”第二代传人张玉亭、第三代张景福、第四代张铭一起在老作坊创作。
2007年,“泥人张”第6代传人张宇先生向天津市档案馆捐赠档案45件,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数其父张乃英先生的4篇手稿。这些手稿的题目是:《泥人张的艺术成就》(1976年)、《泥人张的彩塑艺术》(1978年)、《泥人张的艺术及其作品》(1982年)和未标注写作年代的《张明山的彩塑艺术》。
从题目可以看出,这些评论文字,是张乃英先生对于前人,主要是对前两辈张明山和张玉亭的评价,并针对“泥人张”彩塑作品逐一分析,娓娓道来,总结其现实主义特征。虽然这些文稿已历40余年,但客观、中肯、全面,引经据典且又见微知著,显示出深厚的批评功力。
虽然张乃英先生公开发表的文字并不难见到,但这些手稿还是相当有价值。作为泥塑世家,能自觉地进入研究领域,自省自问,系统地爬梳,有史有论,不同凡响。
“泥人张”是第一批中华老字号,它是艺术,也是商品,是天津的一张名片,是商旅文结合的良好范例,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文化张力。
在传神与传奇之间
可以用“神乎其技”来形容“泥人张”的技法。民国年间宋蕴璞编撰的《天津志略》中记载:“张明山,精于捏塑,能手丸泥于袖中,对人捏像且谈笑自若,从容不迫,顷刻捏就,逼肖其人,故有‘泥人张’之称。”这是志书对“泥人张”的记载,的确突出了一个“神”字。
1947年2月20日《大公报》的“天津人物志”上,有一段纪念张明山的文章:“至其如何工作?不过在观戏时,即以台上角色,权当模特儿,端详相貌,剔取特征,于人不知不觉中,袖中暗地摹索。一出未终,而伶工像成;归而敷粉涂色,衬以衣冠,即能丝毫不爽。”这段文字记载的看戏捏人的情节,在20世纪80年代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泥人常传奇》中使用,且也是强调袖中创作的过程,以显示其“神”。
最早为“泥人张”作传的是天津名流严修。称其“神明其法”,说“其执艺也,优游自得,若不经意”。这也是记录“泥人张”技法传神的滥觞。
的确,历代“泥人张”传人都颇有天分,严修称第一代“泥人张”张明山“全由心悟,并无师承”,虽然从他的父亲张万全即开始捏泥人,但他并未向其父学艺,更未向其子张玉亭授艺。这种技艺的神韵却代代相传下来。
于是,从传神延展到传奇。
“泥人张”本为一高雅艺术,却因从传神延展到传奇的过程里,一度坠落云间。20世纪80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泥人常传奇》是以“泥人张”和葡萄常杂糅为原型的作品,而同一时期天津本地制作的电视剧《泥人张传奇》自然是以第一代“泥人张”张明山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同时使用了“传奇”字样。
这两部作品故事的“梁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张明山“贱卖海张五”,一个是张明山被困于王府最终逃离。虽然叙述手段有所不同,但是大差不差。
美术学者张映雪先生在《泥人张的艺术和生平》一书中也提及这两个故事。海张五邀张明山到家为其塑像,态度傲慢,并因张明山要价过高而抵赖,张明山随即将其塑像略作夸张歪曲,到天津东北城根一地摊贱卖,海张五只能高价收回。慈禧太后曾邀请张明山入宫,皇族奕伯乐叫他到王府创作,因见奕伯乐鞭抽童役,愤而离去。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其人》有《泥人张》一文,即是“贱卖海张五”的故事,和张映雪先生记载的不同,这篇小说是写张明山在天庆馆和海张五相遇,继而发生了情节类似的故事。
“泥人张”本是真实存在的艺人,只因其技之神而获得传奇色彩,进而进入艺术的虚构之中,于是真实的“泥人张”和艺术的“泥人张”割裂开来,其实这是需要厘清讲明的。
在民间与殿堂之间
“泥人张”出自于民间,但是其艺术却并非只在民间。1915年,“泥人张”的16件作品参展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并获得“名誉奖”。这不是一般的民间艺术可以企及的。
严修撰写的《张君明山事略》刊于1921年5月22日《社会教育星期报》上,后收录于《严修先生遗著》和《严修年谱》中。这说明严修和张明山交往甚深,从这一交游来看,张明山并非卖泥人的民间艺人。
严修这样记载:“张君明山,名长林,天津人。天津故有某氏以塑像为世业,君晚出,神明其法,声名突出其上。余应试时,同舍南人审余为津籍,则以泥人张见询,盖驰誉远矣!”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张明山的技法高超,也能看到他的驰誉之远。
而徐悲鸿在1931年抵津,见识到“泥人张”的作品之后,也曾写有一篇文章。这样的绘画大家能亲自撰文关注,足见当时“泥人张”的艺术成就,徐悲鸿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但是,他的文章却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开篇即称:“世多有瑰奇卓绝之士,而长没于蒿莱”,虽然徐悲鸿肯定“泥人张”的艺术成就,但他还是叹息“泥人张”是“没于蒿莱”的。这大抵是因为,泥塑工匠曾处于社会底层,并非正式职业,所制作的也都是游戏小品,不足道哉。
现今的“泥人张”第6代张宇先生的企业名称是天津市泥人张世家绘塑老作坊,这其中的“绘塑”概念,即来自徐悲鸿的建议。他以为“泥人张”的雕塑在彩绘技法中有绘画晕染技巧,这种技巧与传统的彩塑所使用的“随类赋色”的颜色平涂方式区别很大,故而提出“绘塑”之说。
“泥人张”自开始就并非底层工匠,张明山和他的父亲张万全虽都制作泥塑,但他们都是读书人。张宇先生撰文称,“泥人张”是一种带有调侃戏谑的夸赞,是天津人既看不起别人,但是又真诚崇拜有才能人的矛盾心理表现,带有一点儿明贬暗褒的含义。
张宇先生所称,是其谦逊的说法,也带有一丝辩论的成分。在他看来,“泥人张”的确是不同于一般的民间艺术的,它虽操泥塑之艺,却在殿堂之间。“泥人张”的第一代张明山并未以泥塑为主业,他的主要职业是绘画。
有一种说法是,张明山在锅店街创建了塑古斋泥塑作坊,后其衰落不存。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据张棕信先生撰文称,张明山并没有专门的制作作坊,他是随性创作,他的书斋称为溯古斋,作品也全都是出自于书斋,经向张宇先生求证得知应依此说。而“泥人张”自第二代开始,溯古斋成为制作的斋号,有泥塑和绘画作品产出。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泥人张”的第二代张玉亭将泥塑作品委托给估衣街的同陞号售卖,其主人赵月廷是张玉亭和他的六弟张华棠的好友,因寄售方式运营得力,久之同陞号竟然成为“泥人张”的专卖店。这也是“泥人张”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奖名单上被称作“天津同陞号泥制人像16件一份”的原因。故而,在天津也有“张家泥人赵家卖”这样一句俗语。
“泥人张”从一开始的商业路线就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懂得联合,更注重创新,所以才能绵延近两百年不衰。“泥人张”世家的泥塑产品时至今日相对也是比较贵的,它拥有精品意识,打造小众市场,也保持了最初的文化品质。
虽然从题材上来说,“泥人张”贴近大众生活,但它更需要艺术的知音。
徐悲鸿抵津时,在张伯苓带领下来到已故的严范孙家,看到了张明山为严修父亲严仁波制作的塑像,此后撰写《泥人张感言》一文,发表在次年7月1日《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其称“全体结构,若三十年前之照相”,又说:“至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据我在北方所见美术作品中,只有历代帝王画像宋太祖之像可比拟之。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不足多也……”待到同陞号参观之后,又称“此二卖糕者与一卖糖者,信乎写实主义之杰作也。”
“泥人张”的最大特征可能是写实。写实是西方美术的重要元素,而东方则是写意。中国传统泥塑是稍微显得夸张的,带有象征意味,但“泥人张”并非如此,从第一代人就已经接触西方传来的写实绘画和雕塑技术,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直到现在,人们对于天津的文化品牌“泥人张艺术”都存在较大的误读。
清代诗人崔旭和张明山是同一时代人,其在《津门百咏》有诗称:“竹马鸠车不倒翁,太平鼓词闹儿童;泥人昔说鄜州好,可似天津样样工。”古代鄜州泥人有名,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已有记载,而诞生于天津的“泥人张”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却将这一传统艺术推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